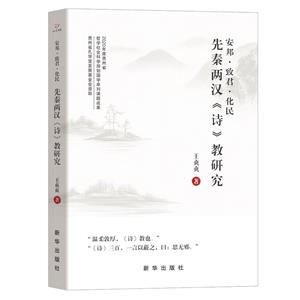-
>
百年孤独(2025版)
-
>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珍藏版全四册)
-
>
心归何处
-
>
(精装)罗马三巨头
-
>
野菊花
-
>
梁启超家书
-
>
我的父亲母亲:民国大家笔下的父母
先秦两汉《诗》教研究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6674529
- 条形码:9787516674529 ; 978-7-5166-7452-9
- 装帧:平装-胶订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先秦两汉《诗》教研究 本书特色
孔子曾云:“温柔敦厚,诗教也。”自《诗经》形成之初,其教化功能已伴随礼乐制度的建立而产生、运行和发展。在古代,《诗经》始终处于政治礼教和国家生活的核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诗经》本身即是完善的知识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而存在。《诗经》之教,春风化雨,浸润无声,在经久不衰的传唱、吟咏与阐释中,以温柔婉转的方式,传播道德伦理,助力社会和谐。本书研究传统《诗》教在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理论构建、文化传播和经世实践,探索传统《诗》教如何在古代政治需求与儒者理想之间构建新的话语模式,尝试以全新视角审视传统《诗》教的价值和意义。
先秦两汉《诗》教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以《诗经》为载体展开的教化研究,探索《诗》教如何在政治需求与儒者理想之间构建新的话语模式,找到新的平衡基点,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诗》教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新发掘经典价值,发挥“《诗》教”在提升国民素养、培育公众德行、和谐社会关系方面的积极功用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先秦两汉《诗》教研究 目录
目录
绪论
**章原始《诗》教形成及实践
**节祭祀制度的革新与《颂》的形成发展
一、殷商时期的祭祀与《商颂》的形成
二、遍祭群神,宣告周兴:《周颂》中的定功、安民诗篇
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周颂》中的记史、颂德诗篇
四、不王不谛,诸侯助祭:《周颂》中的训诫、警示诗篇
五、小结
第二节政治制度的创建与《雅》的形成发展
一、宗法制度与祭祖宴饮之《诗》
二、出使出征与犒劳嘉赏之《诗》
三、王政衰败与讽谏规箴之《诗》
第三节王权的衰落与《风》诗的创作采集
一、采诗途径之一:天子巡狩,大师呈诗
二、采诗途径之二:“行人”与“遒人”以木铎徇于路
三、采诗途径之三:老而无子者民间求诗
第四节小结
第二章德性与政教性:《诗》的两大天然属性
**节以德配天:《诗》中天然的“德”性
一、文王之德:保有天命之根本
二、君子之德,修身之本
三、庶民之德,伦理之源
第二节诗与政通:《诗》中天然的政教属性
一、《诗》从乐起,乐与政通
二、《诗》之兴灭关联于王道
第三节小结
第三章贵族《诗》教的应用与实践
**节贵族《诗》教时代的政治背景
第二节西周教育体系中的《诗》教
一、乐德与《诗》
二、乐语与《诗》
三、乐舞与《诗》
四、乐仪与《诗》
第三节春秋政治体系中的《诗》教实践
一、“歌《诗》”:礼制的遗存与僭越
二、“赋《诗》”:断章取义,德义为先
三、“引《诗》”:脱离乐舞,语义独立
四、春秋时期《诗》教实践的变化与特点
第四节小结
第四章孔门《诗》教:儒家《诗》教的发端
**节礼乐之再造:孔子《诗》教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仁义与王道:孔子对《诗》教的理论贡献
一、从模糊到清晰:首次明晰了《诗》篇的主旨
二、援《诗》说“仁”:孔门《诗》教“内圣”之方
三、王道解《诗》:孔门《诗》教“外王”之方
第三节原则与宗旨:孔子《诗》教的几个关键词
一、思无邪:确立后世儒家系统解《诗》的原则
二、温柔敦厚:划定后世儒家《诗》教实践的宗旨
三、兴观群怨:美刺与讽谏的理论根源
第四节小结
第五章战国《诗》教:儒家《诗》教的发展
**节子思学派之引《诗》、说《诗》
一、子思学派引《诗》之内容
二、子思学派引《诗》之特点
第二节孟荀对儒家《诗》教的贡献
一、孟子对儒家《诗》教的继承与发展
二、荀子对儒家《诗》教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节小结
第六章汉代《诗》教:儒家《诗》教的定型
**节汉代儒家《诗》教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汉代《诗》教的缘起与发展
一、缘起:汉初陆贾说《诗》
二、尝试:文景时期《诗经》学派对黄老学说的冲击
三、鼎盛:元成时期的《齐诗》治国
四、独秀:东汉时期《毛诗》的蓬勃兴起
第三节三家《诗》的理论构建及政治实践
一、《鲁诗》的学术特征:“四始”之说与“诗为谏书”
二、《韩诗》的学术特征:先秦《诗》教的绕梁余音
三、《齐诗》的学术特征:谶纬之说
四、西汉《诗》教政治实践
第四节《毛诗》的理论体系构建
一、《毛诗》的学术渊源
二、《毛诗》确立的系统《诗》教理论
三、《郑笺》对《毛序》的补充和完善
第五节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先秦两汉《诗》教研究 相关资料
绪论
自西周到清末,在近三千年的漫长时光中,《诗》演变为《诗经》,以《诗》为载体的人文教化伴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先民的宗教事务、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教”之名的正式提出,是《礼记·经解》中孔子所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然自《诗》形成之初,其教化功能已伴随礼乐制度的建立而产生、运行和发展,《诗经》在漫长的年代中,始终处于政治礼教和国家生活的核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诗经》本身即是完善的知识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诗经》又作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存在。《诗经》之教,春风化雨,浸润无声,在经久不衰的传唱、吟咏与阐释中,以温柔婉转的方式,传播道德伦理,美风俗而厚人伦,阐明政教之道,规天子而致太平。
可以说,自西周初年《诗》创作产生始,以《诗》为载体的人文教化就伴随着历史政治的变迁,不断丰富、发展和变迁,时代变化赋予《诗》教新的职责和使命,而政治变革则带给《诗》教调整嬗变的新契机。自孔子编订六艺以来,《诗》教作为儒家“六艺之教”之首,其随着时代变迁发展嬗变的过程,既是儒家经典在应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时作出的自我调整和适应,亦是儒家群体“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志向、情怀借由经典的诠释和运用在时代和社会变迁中对保持政治清明、维系社会和谐做出的不断尝试和不懈努力。温柔敦厚、化育无声的传统《诗》教,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社会秩序、培养道德伦理、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发挥过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诗》教”探讨的著述和论文相对较少、较为零散,具有个体性研究、断代性研究较为突出的特点。总结国内“《诗》教”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
绪论
自西周到清末,在近三千年的漫长时光中,《诗》演变为《诗经》,以《诗》为载体的人文教化伴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完善和发展,在先民的宗教事务、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教”之名的正式提出,是《礼记·经解》中孔子所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然自《诗》形成之初,其教化功能已伴随礼乐制度的建立而产生、运行和发展,《诗经》在漫长的年代中,始终处于政治礼教和国家生活的核心地位,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一方面,《诗经》本身即是完善的知识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诗经》又作为中华文明中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存在。《诗经》之教,春风化雨,浸润无声,在经久不衰的传唱、吟咏与阐释中,以温柔婉转的方式,传播道德伦理,美风俗而厚人伦,阐明政教之道,规天子而致太平。
可以说,自西周初年《诗》创作产生始,以《诗》为载体的人文教化就伴随着历史政治的变迁,不断丰富、发展和变迁,时代变化赋予《诗》教新的职责和使命,而政治变革则带给《诗》教调整嬗变的新契机。自孔子编订六艺以来,《诗》教作为儒家“六艺之教”之首,其随着时代变迁发展嬗变的过程,既是儒家经典在应对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时作出的自我调整和适应,亦是儒家群体“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志向、情怀借由经典的诠释和运用在时代和社会变迁中对保持政治清明、维系社会和谐做出的不断尝试和不懈努力。温柔敦厚、化育无声的传统《诗》教,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稳定社会秩序、培养道德伦理、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和民族性格发挥过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诗》教”探讨的著述和论文相对较少、较为零散,具有个体性研究、断代性研究较为突出的特点。总结国内“《诗》教”研究,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诗》教特征、影响等方面的宏观研究。如陈桐生的《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1],从礼学视野出发研究先秦两汉《诗》教理论生成与构建;王启兴的《论儒家诗教及其影响》[2],对儒家《诗》教支配下所形成的文学观和价值观进行了梳理,主要突出了儒家《诗》教政教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张国庆的《论儒家诗教的思想性质》[3],强调《诗》教理念带有汉代儒学的鲜明烙印,与孔子思想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刘怀荣的《论诗教的文化渊源与历史形态》[4],对《诗》教产生的早期文化基础和感性形态进行了追溯与论证,从巫官文化到史官文化发展的历程角度肯定了《诗》教的缘起与发展;林志敏的《儒家诗教的思想本质及哲学基础》[5],对孔子“思无邪”说和“温柔敦厚”说进行比较,得出二者之中“思无邪”更接近孔子《诗》教本质之结论;梁占先的《儒家诗教及其特征》[6]着重谈到了春秋时期“引诗言志”的《诗》教特征;金宝的《论以诗为教的产生于诗教观的确立》[7]概括梳理了《诗》教观的确立历程。这些研究成果或对《诗》教的某一方面的功能、或对某一具体时段的特征有深入的分析,或对《诗》教观的形成追根溯源,其中不乏精彩创见。
二是对某一特定阶段的《诗》教研究。如黄克剑的《孔子“诗教”论略》[8]、延钥的《礼的内在化运动背景下〈孔子诗论〉特征分析》,对孔子《诗》教与仁道,与礼乐之道进行了精彩阐述[9];冯时的《六经为教与儒学的形成——论孔子正〈诗〉与〈诗〉教之重建》[10],对孔子“正经立教”的具体作为进行了阐述分析;周德清的《孔子诗教对于诗教传统的革新》[11],提出了“孔子《诗》教”与“传统《诗》教”两个不同概念,并将“传统《诗》教”定格于尧舜时代,对比了两者的继承与革新;唐定坤的《孔子〈诗〉教视野下的“〈诗〉始关雎”及其阐释转向》,对孔子《诗》教中关于《关雎》的诗旨阐释进行分析,并对其后儒家《诗》教诸家对《关雎》的阐释转向作出细致梳理[12];凌彤的《儒学的分化与战国〈诗〉教的传承》,对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与《诗》教的传承作出了梳理分析[13];郑明璋的《儒家诗教传统与汉赋讽颂》[14]分析了汉代《诗经》学的发展对汉赋中颂美与讽谏两大功能的促进和影响;梁大伟的《汉代的诗教观》[15]阐释了汉儒的经学观念、讽谏思想及诗学观念,分析了汉代与前人《诗》教观的继承关系。这一部分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孔子《诗》教和汉代《诗》教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的《诗》教研究,部分研究成果触及《诗》教的宗旨及核心,在探索各阶段《诗》教的传承接续脉络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中不乏精彩论述。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虽未提出“《诗》教”之名词,但着重于对《诗经》的功能性研究。如,对某部著作中用诗、引诗情况的考证和研究。这一类研究所占的比例较大,学者主要对《论语》《左传》《国语》《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文献中用《诗》情况进行了考证和分析,也有少量文章对《墨子》《晏子》等诸子著作中的用《诗》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这一类研究着重考察在著作中用《诗》的方法及特点,具有文献分析的意义,多从文学角度出发。比如梁大伟的《〈论语〉中用〈诗〉、引〈诗〉和评〈诗〉现象》,李晴晴的《〈左传〉引〈诗〉诗义研究》,斳英的《元代戏曲用〈诗〉研究》,等等。
与论文研究成果一样,目前关于《诗》教的著作成果也多集中对某一时段的《诗》教思想研究,或用《诗》考论、研究中。如王倩所著《朱熹诗教思想研究》[16],对朱熹的《诗》教理论框架和教学体系进行了梳理研究;罗立军所著《从诗教看〈韩诗外传〉》[17],探讨了治道与《韩诗》中的教化原则、历史构造和礼制思想;俞志慧所著《君子儒与诗教》[18],系统探讨了儒家的“言语”之内涵范畴与先秦《诗》教思想的形成建立之联系;王秀成所著《三礼用诗考论》[19]、陈致所著《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20]、马银琴所著《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21]、战学成所著《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22]、周泉根所著《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23]等。王秀成的《三礼用诗考论》对典礼制度与《诗》的关系进行系统考证,通过一系列与“礼”相关的文学问题和与“诗”相关的礼学问题的研究,解释了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规律,涉及周代《诗》的宗教功能和乐用功能;陈致的《诗经的形成》一书结合国外音韵学研究成果和国内考古成果,对《诗》的分类和编排提出了创造性的意见,对《诗》与“乐”的紧密联系做出了细致翔实的考证,有助于我们了解《诗》在形成初期的乐教功能的具体实现;马银琴的《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对《诗》的文本在周秦时代的传播和应用做了分阶段、分地区的翔实论述,对诗乐分离时期的春秋赋诗、引诗现象进行了结合历史背景的客观分析;战学成的《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的社会生活》以诗的创作和应用为切入点,独创性地将周代分为诗的创作和诗的应用量大部分,对诗经中的诗篇中所蕴含的礼乐背景进行了详细研究;周泉根的《新出战国楚简之诗学研究》以郭店楚墓战国竹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为研究对象,研究《诗》和“言志”之间的文献学、文化学和文字学关系,探讨礼乐文明与诗之关系,揭示《诗》的经典化、本位化和政教化的过程,考镜源流,论证严密。郑伟的《毛诗大序接受史研究》[24]以《毛诗大序》的接受史为切入点,用文化诗学的方式勾勒出古代儒学文论的演进逻辑及阶段性特征,特别关注时代问题与经学教育体制对士人主体精神的深刻影响,其结合历史背景研究儒学文论的研究方法对开拓笔者的研究思路提供了较好的借鉴。
国外对《诗经》的功能性研究集中在运用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中的篇章与节庆、信仰、习俗与巫术的关系。其中代表学者为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hel Granet),他在《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25]一书中,探讨了《国风》篇章与中国古代节庆、歌舞、信仰与习俗的关系。此书开启了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之肇始。美汉学家周策纵所著《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26],讨论了古巫医与《诗经》中篇章之关系。美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著《〈诗经〉中的繁殖与再生》[27]从《诗经》中诗篇内容出发,讨论了社会生产与种族延续、社会结构与政治伦理延续之问题。日本学者接受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诗经》研究方法,许多学者在此领域有所建树。赤冢忠在《古代歌舞诗的系谱》[28]中提出“三百篇”大部分为歌舞之诗,而“兴”之意,原本是由咒术所产生的;白川静在《诗经的世界》[29]中从民俗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经》篇章,力图还原中国古代社会与生活的原貌。
可以看出,国外学界目前对《诗经》的功能性探讨主要集中在《诗经》中所反映出的先秦时期社会生活礼俗的相关研究上,对《诗经》脱离音乐之后纯文本的传播和诠释,尤其是儒家《诗》教的功能性研究相对缺乏。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诗》教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一是整体来看,对《诗》教缺乏整体的视野和明确的定义。“《诗》教”与“《诗》教”概念并未得到清晰划分,出现混用的情况。“《诗》教”,侧重于以《诗经》经义阐释和践行而达到淳风化俗、致君尧舜、致力太平之政教功能;而“《诗》教”,则是包括《诗经》但不限于《诗经》的诗歌之教化,侧重于其文学、艺术和审美等功能。两者应得到清晰划分和区别使用。然从目前学界对其的使用上来看,尽管所言乃以《诗》为教的“《诗》教”,多数学者仍然使用“《诗》教”以代之,当然已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区分,用“《诗》教”指代以《诗经》为蓝本的儒家之教。从上文的文献梳理中即可明显看出此状况;二是对《诗》教的研究缺乏历史纵深的整体视野观照。《诗》教形成的历史背景、文化渊源探讨有待进一步深入,各阶段《诗》教之间的传承接续脉络研究仍然比较缺乏。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诗》教的形成动因、内在属性、演变脉络有待进一步探求。
因《诗》教本身具有的动态性、扩展性和实践性,厘清《诗》教的形成渊源、发展脉络、演变动因实在殊非易事。本书尝试在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以古代历史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转型为研究背景,追溯《诗》的原始政教性创生动因,探寻历代《诗》教发展演变中所延续的内在脉络和逻辑关系,思考在朝代更迭、政治变革的转型时期,《诗》教如何顺应历史潮流和政治环境,自我调整、因循变革而不断演化延续的内在动因,期望能在整体视野下梳理出一条从《诗》教之发源到儒家《诗》教之定型的连续脉络。因学识所限,文中偏颇不周之处在所难免,不免有武断之语,唯期方家指正赐教。
引论:《诗》教之概念
最早出现《诗》教的文献是《礼记·经解》,其中记载了孔子关于《诗》教的言论:“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后世谈及《诗》教,多沿用此语。然“温柔敦厚”,可视之为《诗》教的方法和《诗》教的目的,但对于什么是《诗》教,如何教之,孔子并没有言明。
到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对《诗》教作出了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30]。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之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故云深于诗者也。[31]
又云:若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则是深于诗者也。[32]
孔氏所疏,一方面是对孔子所论“温柔敦厚”的词句阐释,一方面是承接《诗大序》中提出的美刺观,对《诗》教的“教人”的功用性进行阐述,指《诗经》阐释以义理为主,赋予政教得失之意义,以美刺讽喻以“教人”。然对于《诗》教的方法、目的和效果描述仍然十分模糊。这个问题在后世一直存在,后世儒家学者多直用《诗》教之名,却少有人对《诗》教的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谈及《诗》教,也多是讲其功用效果。如苏洵在《嘉祐集》中云:“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3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中云:“故《诗》之教,理性情,明劝戒,其道至大。”[34]所言还是《诗》教在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方面发挥的作用。
当代学者也对《诗》教的概念进行过探讨。康晓城提及两汉以人伦教化说《诗》,阐述《诗》教具有和谐人伦之重要功能:“因儒家之学,特以明人伦为宗,由于诗具有敦厚、和谐人伦之功能,故《诗》教甚受重视,尤其孔子以后之战国两汉儒者,以人伦教化说诗,将诗运用于政教。”[35]强调是儒家《诗》教的重要社会功能;刘文忠在《温柔敦厚与中国诗学》一书中也谈到了《诗》的教化:“孔颖达对‘敦厚’二字并未作出解释,却将《诗》的依违讽谏,不切指事情抛出,这实际上是为《诗》的讽刺原则进行了一种规范,即在运用诗歌表达感情的时候,要言辞温和、性情和柔。这就是《诗》的教化。”[36]其实所言,仍然是对“温柔敦厚”的理解,所言乃是《诗》的教化方式。夏静、李轶婷在《诗教制度论》中简单对《诗》教做出定义:《诗》教,“是指以《诗三百》为载体的人文教化,为‘六艺之教’之首”。[37]以“人文教化”概括《诗》教,固然不错,但概念范围显得过大。
《诗》教,顾名思义,即是指“以《诗》为教”。既然以《诗》为载体进行教化,就涉及教化对象、教化方法、教化目的和教化效果。孔子所提出的“温柔敦厚”,按照历史上诸家的理解,可视作教化目的,亦可视作教化方法。但这只是《诗》教概念中的一个因素,不能代表《诗》教的全部。后世提及《诗》教,多从“温柔敦厚”之语扩展引申,实为儒家《诗》教之内涵意义。但其实自《诗》产生之时起,以《诗》为教的活动已经随着西周王朝典仪、教育而蓬勃展开,以“温柔敦厚”为典型特征的儒家《诗》教,其实只是《诗》教生成、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林耀潾所言,“郊庙祭祀、燕享宾客,必奏诗乐以成礼,此诗、乐、礼三者相须为用之状也,及其后,诗脱离礼乐,仅以诗辞美刺讽喻为教,然三者合一之时,亦《诗》教也。”[38]此说即看到历来学界多以儒家《诗》教混淆《诗》教整体概念之误区,将西周时期诗礼乐一体的教化活动亦归入《诗》教之整体内涵。然若从《诗》之产生过程来看,《诗》教之实际内涵还可再往前推至西周之初。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诗》教亦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延展其内涵,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之后,当我们以纵贯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研究《诗》教,有必要对其进行概念的重新界定。
在对《诗》教进行定义之前,笔者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
其一,“《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的变革、社会的变迁,有一个不断完善、丰富和改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诗》教的内涵与外延皆不相同,其演变与发展,与政治变革、社会发展多因素推动密切关联。
其二,“《诗》教”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正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诗》教观念都不相同,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诗》教进行单一定义。它应该是包含了许多子概念的一个系统的概念。关于“概念”的设定动因,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布迪厄曾提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其三,“《诗》教”之教,既是孔教之教,亦是教化之教。因此《诗》教的概念中,既包括理论的构建,又包括教化的实践。在这样的设定目的之下,我们定义《诗》教这样一个动态性、实践性、系统性的概念,就应该从实际研究的功用出发,对《诗》教的整体概念和与之关联的各个子概念进行全面的定义。
正基于此,《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不同时代的《诗》教概念有所不同,而《诗》教实践与《诗》教理论的衍生发展又相互交织,要阐释《诗》教的概念,涉及交替使用共时分析与历时分析的不同方法。
我们从《诗》的起源开始,来看看《诗》教的最初形态。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自孔子明确提出《诗》教的概念后,《诗》教才逐步形成。但事实上,自《诗》形成之日起,《诗》已经肩负着教化的功能,是周王朝维系政权稳定、教化诸侯百姓的重要工具,其实践性在其创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西周初期,为配合新建立的周王朝明确政权合法性、强化宗族认同感、威慑四方异姓诸侯的政治需求,《诗》中《周颂》《大雅》中的篇章应运而生。《周颂》中古朴简短、雄壮有力的诗句,配合各类祭天、祭祖的宗教仪式,传达出周人“受命于天”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彰扬了自后稷到文王的高尚品行与伟大功绩,警示了四方异姓诸侯顺应天命,恪守臣道,此时期,《诗》的教化对象包含了西周社会的各个层面:受封的周人的血亲诸侯、殷商旧民与上层诸侯臣僚、其他宗族的诸侯与四方百姓,教化的宗旨是安抚、引导与警示,最终目的是维护新生政权的稳定和权威。西周中期,随着政治制度和礼乐制度的逐渐完备,伴随着燕享、征伐、嘉赏、出使等国家大事的发生,配合政治事件与礼乐的推行,《诗》中《大雅》的小部分诗篇和《小雅》中大部分诗篇应运而生,伴随着礼乐的传播和深入,这些配合礼乐反复吟唱的篇章起到了凝聚邦国对王朝的向心力、聚拢和稳定百姓的民心、传播关于人伦的秩序和人性的美德等重要功能,对维护社会秩序、培育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此阶段,教化的对象是西周百姓。《大雅》中有一部分诗歌作于厉王时期,《小雅》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诗歌作于宣王、幽王时期。这些诗篇多为讽谏之诗,是当朝公卿大夫针对君王的失德、王政的弊端进行的哀叹和讽谏。这些诗篇“教化”的对象直指君王本身。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风》诗中大部分诗篇出现,反映百姓生活、情感的诗篇彰显了王道政治的兴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而这一部分《风》诗,被采集于《诗》的最初目的是“观风俗”“知得失”,作为君王资政的参考,但鉴于周王室日益衰落的现实,本来针对君王的“教化”失去了其本身的功能和意义。
在孔子之前,西周早期的教育体系中,也早已有以《诗》为教的实践。这一阶段《诗》教的概念虽未正式提出,但《诗》之教也附着于“乐”之教,作为“乐教”中表情达意的文辞部分承担着传播礼乐教化、规范社会秩序、行使政治使命的部分功能。此阶段的《诗》教,即是“雅”教,贵族教育的主要方面之一。贵族阶层的子弟通过诗乐一体的教化,使得仪容风度、言谈举止、内在修养都符合“礼”之标准,能够满足政治生活的朝聘会盟中出使专对、国事交流等整治活动的实际需要。有赖于《诗》本身具有的“德”性,“乐教”中以《诗》的文辞歌颂圣王、教化人伦、传播美善,同时有赖于《诗》中天然的“政教性”特质,上层贵族以《诗》为社交手段、说服利器,完成政治生活领域中诸如规谏、请求、斡旋、威慑等诸多政治功能,在歌舞揖让、引诗赋诗中完成政治使命,促成国家大事,这也是《诗》教发展中重要的一个阶段。
自孔子之后,“《诗》教”具体为“儒家《诗》教”,此后每一个阶段的《诗》教发展,都伴随着儒家知识分子所做出的《诗》教实践。儒家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变迁中秉承着济世救民的理想情怀,努力适应时代发展与政治变革,以《诗》为谏积极入世的行动实践,既是对《诗》教理论的践行,其过程也为《诗》教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先秦两汉《诗》教研究 作者简介
王贞贞,1982年生,四川成都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越南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现任西华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泰国格乐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儒学。
- >
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
¥14.4¥42.0 - >
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精装
罗曼·罗兰读书随笔-精装
¥32.9¥58.0 - >
巴金-再思录
巴金-再思录
¥15.7¥46.0 - >
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
¥19.1¥42.0 - >
烟与镜
烟与镜
¥18.3¥48.0 - >
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
¥16.7¥39.8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6.7¥19.0 - >
莉莉和章鱼
莉莉和章鱼
¥14.4¥42.0
蔬果篇-结构静物-实物照片+步骤解析+训练要点-临摹本
¥10.5¥15.0当代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24.8¥34.0百年道路:《生死关头》二集
¥44.7¥59.0元禄忠臣藏
¥13.7¥28.0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12.3¥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