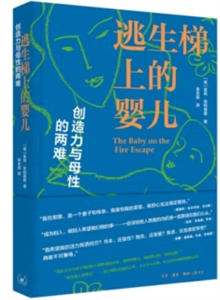-
>
百年孤独(2025版)
-
>
易中天“品读中国”系列(珍藏版全四册)
-
>
心归何处
-
>
(精装)罗马三巨头
-
>
野菊花
-
>
梁启超家书
-
>
我的父亲母亲:民国大家笔下的父母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版权信息
- ISBN:9787108076243
- 条形码:9787108076243 ; 978-7-108-07624-3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本书特色
厄休拉·勒古恩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富有成效的稳定性,奥德雷·洛德按照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卡特分别在19岁和43岁的时候成为母亲。这些母亲育有一个孩子,或五个,或七个。她们在工作室、在厨房、在车上、在床上、在书桌前创作,婴儿车就放在她们身边。作者以强烈的共情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些20世纪杰出的艺术家、作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私密抗争。她们因为追求创造性的工作而遭受指指点点——多丽丝·莱辛被指责说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爱丽丝·尼尔被婆家说成为了完成一幅画,把孩子丢在纽约公寓的逃生梯上。
菲利普斯把这些开创性女性的生动画像穿插在一起,提出具有创造力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把婴儿放在谣传中的逃生梯上的问题:工作和照护处于一种不断协商、临时的、生产性的张力之中。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内容简介
厄休拉·勒古恩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富有成效的稳定性,奥德雷·洛德按照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卡特分别在19岁和43岁的时候成为母亲。这些母亲育有一个孩子,或五个,或七个。她们在工作室、在厨房、在车上、在床上、在书桌前创作,婴儿车就放在她们身边。作者以强烈的共情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些20世纪杰出的艺术家、作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私密抗争。她们因为追求创造性的工作而遭受指指点点——多丽丝·莱辛被指责说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爱丽丝·尼尔被婆家说成为了完成一幅画,把孩子丢在纽约公寓的逃生梯上。
菲利普斯把这些开创性女性的生动画像穿插在一起,提出具有创造力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把婴儿放在谣传中的逃生梯上的问题:工作和照护处于一种不断协商、临时的、生产性的张力之中。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目录
“她自己身体的主宰”
母亲中的“不法之徒”:爱丽丝·尼尔
时时刻刻:艺术怪物与维护工作
不适区:性与爱
矛盾的快感:多丽丝·莱辛
不适区:不可得的缪斯
“诗歌即家务”:书本 VS 婴儿
幸福的家庭:厄休拉·勒古恩
不适区:幽灵
不适区:大器晚成
母亲、诗人、战士:奥德雷·洛德
不适区:心有旁骛
自由:艾丽丝·沃克
书桌上的婴儿,或一心二用
她自己的路数:安吉拉·卡特
时间和故事
致 谢
注 释
参考文献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节选
时间和故事
找一个支持自己的伴侣。自食其力。先生孩子,再干事业。先干事业,再生孩子。赚钱。靠福利生活。生一个孩子,或者三个、七个。关上门来工作;在客厅里画画;把孩子放在书桌上,工作时有孩子在身边。
“我怎么在生孩子的同时不牺牲我的事业、我的判断力、我的独立性、我的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唯一的。从本书论及的女性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做个“母亲中的不法之徒”,或是让朋友帮忙是有益的。
不过,本书论及的女性绝对必须拥有的东西只有两样。毋庸置疑,其中之一就是时间。她们需要工作时间;需要合理规划时间;需要一种方法去遵守资本主义的残酷公式,即时间就是金钱。她们活在灵光乍现的时刻里;在失败的时刻学习;紧盯着将母性与创造性困于生产性张力的时钟。
母性时间是爱丽丝·尼尔和安吉拉·卡特“姗姗来迟”的为人母的时间。它是勒古恩既当作家又当母亲的时间;是拜厄特持续悲伤的当下,是洛德迎来变化的未来。它是剥削性的时间贫困,使得艾丽丝·沃克的母亲远离自己的孩子和花园。停滞的事业陷入时间的暗流。它是靠安非他明加速的时间。它是孩子们离家之后的涣散时间。
它是芭芭拉·赫普沃斯的每天半小时,“让图像在脑海中生长”。它是洛德装在尿布袋里的诗歌碎片和迪·普里玛“时光的幕布”出现裂缝,让自我的时刻得以显现。它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坚忍和爱丽丝·尼尔的坚持。它是联邦艺术计划给予尼尔的时间,也是古根海姆的资助给予艾丽丝·沃克的那一年,使得她能够逐渐了解《紫色》中的人物。它是托妮·莫里森在孩子们醒来之前起床写作的时间,也是勒古恩不太在乎的时间—因为她的孩子也老是醒过来。它是海蒂·琼斯(Hettie Jones)因为心乱如麻无法写作的时间,用俄罗斯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的话来说:“一个人需要时间,是为了感受,而非为了思考。”
除了时间,一个有创造力的母亲必须拥有的第二样东西是自我。她需要界限和信念,即她有权利创作她的艺术。她不需要把自己过多地交付给他人。
作家克莱尔·戴德勒(Claire Dederer)是魔鬼的拥护者,她把创造性的工作称作一系列“微不足道的自私。把家人关在门外的自私……忘掉现实世界,从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自私……把*好的自己留给不曾谋面的无名爱人—读者—的自私。就只是说出自己必须说出的话的自私”。
不过,她所描述的是自我的时刻,他人被搁置的时刻,婴儿被放在
逃生梯上的时刻。
有一段时间,我脑海中母性自我的样子源于赫普沃斯的艺术,特别是她的一系列小型石雕,名为《两个形式》(Two Forms)。其中一件是在1937 年,也就是她的三胞胎三岁那年创作的。这件作品由两块直立的白色大理石组成,一块稍大于另外一块。它们非常光滑,完整如初,自成一体,彼此相邻而立又不相接触。它们似乎满怀一种人类的渴望,渴望与另一个人亲密无间,同时又把自己紧锁于一种冷酷、周密的孤独之中。
我认为这些形状内含一种必要的空虚,也就是艾德里安娜·里奇称之为艺术之“母体、原型”的“空虚”。勒古恩笔下的这个空间是潜在的,如罐子装水一般,它是承载真理的容器。赫普沃斯一些*美的雕塑都是圆形的、空心的,中间穿着紧绷的线。在我看来,这也是母性的,讲述强烈的情感、强烈的控制,以及即便有其他的爱好,仍然难以抑制的对艺术的承诺。
在去看赫普沃斯展览的路上,我的朋友宁克·亨德里克斯(Nynke Hendriks)说到她不看自己母亲的日记,尽管日记是母亲留给她的全部。“我觉得,我妈妈始终都对自己有所保留。日记是不属于我们的那部分她。”
在其他时候,我认为为人母是如此的宽泛,如此充满了不同的经验,它似乎并不自成一体,而是像个装满了故事的容器。勒古恩在她的文章《小说载体理论》(“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写道,英雄的原型是作为猎人的男性,像一支箭跟随“叙事的弧线”射向目标。这是一个创造性生活的故事:学习技艺、克服障碍、尝试、失败、成功,所
有这些都发生在命运和变化的时间里,希腊人称之为 Kairos* ,即箭射离弓弦,飞在空中的时间。
走出这一叙事的是收集者。收集者找到了有用的零七八碎,并利用更为古老的发明,即袋子或网,把零七八碎的东西带回家。装东西的袋子可以是一个关于母性的故事,在时间(chronos)中发生,漫长的时间。这些时间会孕育出不连贯的思考,有关身体、性、自我和时间本身。在我继续收集逸事、观察,以及搜集一切吸引我注意力且有用的东西时,我试图让这本书成为一个袋子,装着母亲的思考和经验,快乐与痛苦,自我丧失与自我创造。
但*后,我认为无论是被雕刻的自我还是大包的东西都不太对。即便是母亲的故事也仍然需要时机,需要运动,需要女英雄。
在我*初开始把为人母视作一场英雄之旅时,我想知道是否有人把母亲写成女英雄—在自己的生活中航行(或战斗)的奥德赛,在成长或变化的决定性时刻成为母亲。
然后,我意识到我知道一些以母亲为中心的非常古老的故事。我一直以为这些故事有关青春期或婚姻,直到我重看它们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从此之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后的部分。
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磨坊主的女儿被赋予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做了一件好事,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并嫁给了国王。但在她丈夫的城堡里,她要保持坚强,不失去自我。结婚一年后,帮助过她的侏儒回来了,要求她用**个孩子来报答他。聪明的她走进森林,知道了他的名字,并运用自己的知识要回了孩子,夺回了自己的母亲身份。
《侏儒怪》(Rumpelstiltskin)中磨坊主的女儿就是尼尔、莱辛、桑塔格,她们走进了一文不名的婚姻,以为自己会无比尊贵。她们在自己还不够强大,无法同时拥有孩子和事业的时候有了孩子。她们首先需要离开家,并获得更多的知识—关于世界,关于她们自己,关于她们婚姻交易中的暗面。但对尼尔和莱辛来说,自持来得太晚了,她们都没能夺回自己的长子。
女孩从邪恶的继母那里逃了出来,克服了种种障碍,嫁给了国王。但在她生下一个孩子之后,继母伪装成护士,来到皇宫杀了她,让她的独眼继妹代替了她的位置。年轻的母亲成了一个幽灵,在城堡中徘徊,夜里给孩子喂奶,直到国王看见并认出了她。在他认定她是真正的皇后之后,她又活了过来。
《兄妹》(Brother and Sister)中的女孩是被母亲毁掉的伊丽莎白·斯玛特和雪莉·杰克逊,是不被自己母亲承认的桑塔格和沃克——她们的母亲本身就是自毁性的。[在一篇优秀的文章中,艾伦·斯坦伯(Ellen Steiber)把继妹的形象解读为内化的童年创伤,即“自我的独眼 冒名顶替者”取代了真实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这些女性都寻找伴侣来承认她们,并帮助她们,让她们不要在母亲身份中失去自我。但是,正如沃克和卡特得到的教训:要从那个幽灵般的状态回来,你必须要承认你自己。
女孩的父亲砍掉了她的双手。(因为乱伦与魔鬼达成的交易:原因因人而异。)她离开了家,在森林中徘徊,直到她走上了一条通往皇家果园的路。在果园里,王子看到她像个野生动物一样,在吃掉落在地的水果。他觉得她貌美如花,迎娶了她,她生了个孩子。
然后,她的丈夫去旅行,他的家人受到诱骗,要将她遣送离开。这个没有手臂的女人把婴儿绑在自己的后背上,回到了森林。这一次,她找到了自己的路,她的手臂重新长了回来。在一些故事的版本中,一位天使给了她手臂;在另外一些故事的版本中,她的孩子掉进了水里,当她伸手去抓孩子时,她的手臂长了出来。当她的丈夫经过漫长的寻找终于找到她,并带她回家时,她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母亲身份,获得了自己的力量。
《无臂少女》(The Armless Maiden)是每位作家母亲或艺术家母亲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中的每个女人都在森林中迷失过,每个女人也都学会了重获自己的力量—无论是通过照料孩子,还是拥抱自己的缪斯。无臂少女的孩子可以象征一个女人的创造力,如米多丽·斯奈德(Midori Snyder)所写的:她学会运用的天赋,她所接受的职业。但在我看来,它既象征着这二者,也象征着她学会了在不失去自我的情况下为人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躲进森林—每每在她遇到危机,需要艺术灵感或希望重拾自我时。这是母亲英雄获得能动性、权力和自我身份的旅程—每次她都背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生命从森林里走出来,然后又重新获得这些。
这本书花了太多的时间。我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孩子还在上小学。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上大学了。他们因为计划的改变或漫长、迟缓的疫情期而在这个房子里进进出出。他们的衣服不会再因为长高而穿不上了,尽管他们的身体在时间中的成长仍然用铅笔标记在我家的厨房墙上,形成一座垂直的时钟。
*近,我的女儿问我说:“你花了多长时间把我生下来?”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十二个小时?十一个小时在等待,再加上一个小时因为羊水破裂,原计划乱了套,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了。为什么分娩要用小时来衡量,而不是以叙述的章节来衡量呢?我是否应该告诉她,在我不知所措、承受不住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膝盖紧并在一起,拒绝继续生产。
我不认为可以把写书比作分娩。我拒绝认为这二者是等同的,尽管在我交稿的前一天晚上,我确实因为突如其来的压力吼了我丈夫,跟我因分娩痛不欲生时吼他如出一辙。不过,我觉得以一个开始来结束是对的;毕竟,它们都的确发生在我的生活中,婴儿和书本,都远远过了它们的预产期,打消了我*后的犹疑,这本书如今就要写完了。我的女儿在一个下雨
的周二下午出生,助产士轻轻地对孩子的父亲说:“过来吧,要生了。”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相关资料
《逃生梯上的婴儿》考察了20世纪一群鼓舞人心的作家和艺术家母亲的生活,驳斥了所有关于创造力和完全独处的既有观念。茱莉·菲利普斯审视了从格温德琳·布鲁克斯到露易丝·布尔乔亚,从雪莉·杰克逊到苏珊·桑塔格等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她们拒绝在知识的严谨和母亲的身份之间做出选择,同时发现,是她们主张自我中心地位的勇气定义了她们艺术家的身份。太精彩了!
——克里斯·克劳斯(作家、艺术评论家)
在遇到厄休拉·勒古恩之前,我对于一个有孩子的女人如何同时成为作家,没有任何参照的榜样。我拥有的只是孩子。在这里,茱莉·菲利普斯以她一贯的清晰、同情、细致和敏锐,向我们最钦佩的一些艺术家提出了问题:母亲身份与艺术创作对创造力的要求如何挫败又支撑着她们。
——凯伦·乔伊·富勒(作家)
作者富有同情心、思路清晰、惟妙惟肖的文字推动了我们长期以来深为困扰的关于母性与艺术的文化对话。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与母亲的生活。
——帕梅拉·埃伦斯(作家)
逃生梯上的婴儿: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 作者简介
茱莉·菲利普斯(Julie Phillips),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获得者,是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专注于性别与创造性工作之间关系的问题。她为许多杂志和平台,如4Columns、LitHub、《纽约客》等撰稿。
- >
诗经-先民的歌唱
诗经-先民的歌唱
¥14.5¥39.8 - >
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
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
¥14.1¥32.0 - >
姑妈的宝刀
姑妈的宝刀
¥15.7¥30.0 - >
李白与唐代文化
李白与唐代文化
¥9.9¥29.8 - >
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
¥16.7¥39.8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6.7¥19.0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6.7¥68.0 - >
名家带你读鲁迅:故事新编
名家带你读鲁迅:故事新编
¥13.0¥26.0
植物大战僵尸2机器人漫画·无限危境
¥28.4¥45.0跟妈妈玩童谣
¥8.2¥19.0锐势力·名家小说集:有个叫颜色的人
¥35.8¥58.0我们生病了
¥26.2¥35.0感知与观察-《学习小蜜蜂》学前准备手册-1-4至6岁儿童适用
¥5.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