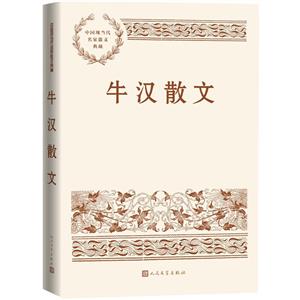-
>
野菊花
-
>
我的父亲母亲 - 民国大家笔下的父母
-
>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965-1966
-
>
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1959-1960
-
>
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1957-1958
-
>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
-
>
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1949-1953
牛汉散文 版权信息
- ISBN:9787020167272
- 条形码:9787020167272 ; 978-7-02-016727-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牛汉散文 本书特色
以质朴而庄严的质地,提升了中国当代散文的质感 ——牛汉散文导读 如果文学界也像当年的法国绘画界那样举办散文的“落选者沙龙”,牛汉(1922—2013)很有可能名列其中。这当然首先因为他作为诗人的名声过于显赫,遮掩了其他方面的成就,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散文写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并不体现在一般所说的表现形式上,他既不刻意谋篇布局,也无意雕琢辞藻,行文如云如风,或者更像从高山上奔腾而出的瀑布,在荒原里无尽燃烧的野火,率性而为,自然天成,完全不设置甚或是有意摒弃具有高辨识度的所谓“风格标记”,自然不易被习惯于“散文”特别是“美文”常规的阅读者所体会,而这正是牛汉散文的特色之所在。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经有了半个世纪诗龄且年近七旬的牛汉开始集中精力写作散文,尽管其中仅有两篇加了“童年牧歌”的副题,但因为这组作品大都围绕着作家的童年生活和故乡的人情风物展开,问世以来即被视为一个有整体联系的系列。而在这组作品发表当时,就有评论者注意到,其间既无暮年的怀旧情绪,更没有任何激情颓落的迹象,显示出来的是不亚于一个作家鼎盛之年的强劲创造力(参见杜丽:《诗人的再生——读牛汉的散文》),这可谓是敏锐而恰且的判断。牛汉本人则说:“我不是返回童年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童年世界。”(《诗和散文都是我的命》)。这是对进入他的散文世界的一个重要提示。牛汉所说的“创造”,当然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童年牧歌”和所有的回忆性散文一样无可避免地包含着虚构成分,更是在说,这组作品的着力点并不在于怀旧忆往,而是作者站在浓缩了数十年火与血般的人生经验之上,重新瞩望自己的人生原点,所做出的深沉思索和再度感悟。这决定了这组散文的结构方式:有意识地把“现在之我”和“童年之我”并置对观,在表面层次,看似是从“现在”的视角追忆过去,而在深层次里,则是借助“童年”之眼凝视乃至审视童年之后长长的“现在”,并把内心里的理想渴求投射到“牧歌”意境的营造上。 就此而言,《离别故乡》无疑是“童年牧歌”系列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篇。此篇既是作者与故乡和童年的告别曲,又是迈向独立成人之路的赞歌,笔墨酣畅,语调悲怆,在情节脉络上相当于整组散文的终章,而在轮廓鲜明的民族救亡大背景上,刻写个人的命运变化和倔强成长,这写法本身也标示了牛汉的思想和写作从早期到晚期的一惯性。牛汉从1940年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歌时候起,即投身到左翼的革命文学潮流之中,数十年历经坎坷遍体鳞伤而其志无改,他晚年写作的“童年”系列散文和他的诗作一样,并无意经营超然世外的闲适境界和充满闲情逸趣的故事,他所创造的“童年世界”,是和人间社会的苦乐悲欢息息相通,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大潮血肉相连的世界。而牛汉的特异之处在于,他从不以公式化的“时代”或“革命”概念去切割或界定个性的人,而始终坚持从人的切身经验,从人的个性的丰富发展和自由张扬去理解和展现时代与革命,在此意义上,《送牢饭和公鸡打鸣》可谓是一篇典型的文本。题目看似两件互不搭界事情的超现实主义式的连接,身陷囹圄的舅舅——一位知识精英型的共产党人,属于牛汉走向革命的启蒙者,但他在牢房里留给牛汉的深刻记忆,却不是通常可以想见的英勇行为和言辞教诲,而是意外地让外甥学公鸡打鸣,并且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参与进来,“鸣唱得十分尽兴”,甚至“流出了眼泪”。如果说当时牛汉对此印象深刻可能出自童稚的好奇,那么,几十年后,自己也多次经受了牢狱之灾,牛汉用文字重述这一情景,状写公鸡鸣唱的声音和气势,特别是对其在黑沉沉的黎明之前倾注整个生命纵情歌唱的浓重渲染,显然具有了更为深长的意蕴和象征意义,甚或可以说,是对革命和革命者应有境界和生命状态的重新塑型。 牛汉的散文当然不限于“童年牧歌”,他的怀念师友之作自然成为另一个系列:胡风、雪峰、聂绀弩、萧军、艾青、路翎、吕荧……,都是左翼革命文学行列里的著名人物,都毫无例外地命运多舛而始终葆有高贵人格和自由不羁的精神,牛汉和他们命运与共的际遇,使得他下笔格外凝重迟滞,他说:“雪峰同志的一生,有如山脉一般的起伏,山脉一般的壮丽”(《以心灵关怀心灵》),但他仅仅记录了“雪峰和吕荧的*后一段友情”。聚焦于山脉的一角,把更多的内容浓缩在文字之后,是这组散文的一致特色,而那些浮雕般呈现出来的情景、细节和意象,因为作者一直铭刻在心,酝酿已久,血肉相连,如他所激赏的艾青的《吹号者》吹出的带着纤细血丝的号音,写出来便具有特别的震撼力量。应该把这组散文和“童年牧歌”系列对读,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牛汉直到晚年也绝不肯做所谓士大夫文人状,而是直向荒凉贫瘠的乡野寻找自己的根;也才能更好地体认,为何牛汉会那样诚挚地为僻居乡间的亲人们献上心曲,那样虔敬地为像大地一样默默无言也默默无闻的底层人物宝大娘、秃手伯造像。他曾这样评价艾青:“他的所有的诗都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一颗不灭的诗星》)这评价同样可以移到牛汉本人身上。 牛汉对底层普通人的挚爱几乎与生俱来,经过左翼革命文学的滋养而更为发扬,并深深渗透到了他的修辞表现里,尤其是在“童年牧歌”系列,他近乎迷恋地从故乡“母语”里汲取营养,而那些带着浓郁乡野气息和蓬勃生机、无法被现成的词典所定义的词语:绵绵土、砍山鞋、灯笼红等,在他的散文情境中,都成为了“诗眼”般的意象。在诗歌写作领域,牛汉自觉追随艾青的传统,努力从鲜活的日常口语里提炼诗的韵律和节奏,他说:“口语是*富于人性的亲切感的,是直接从心灵里流出的脉息”。(牛汉《不可遗忘的声音》)他的散文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追求,且因其广阔的包容性而显得更为汪洋恣肆元气淋漓。牛汉的散文数量不多,但多为精品,以质朴而庄严的质地,提升了中国当代散文的质感。 王中忱 2022年1月16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牛汉散文 内容简介
《牛汉散文》 牛汉的散文如高山上奔腾而出的瀑布,如荒原里无尽燃烧的野火 童年牧歌系列,以质朴优美而庄严的质地,提升了中国当代散文的质感。 (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 【作品评价】 如果文学界也像当年的法国绘画界那样举办散文的“落选者沙龙”,牛汉很有可能名列其中。这当然首先因为他作为诗人的名声过于显赫,遮掩了其他方面的成就,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散文写作方面所做的探索,并不体现在一般所说的表现形式上,他既不刻意谋篇布局,也无意雕琢辞藻,行文如云如风,或者更像从高山上奔腾而出的瀑布,在荒原里无尽燃烧的野火,率性而为,自然天成,接近不设置甚或是有意摒弃具有高辨识度的所谓“风格标记”,自然不易被习惯于“散文”特别是“美文”常规的阅读者所体会,而这正是牛汉散文的特色之所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王中忱 “这几年,我不是返回童年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童年世界。” 牛汉是在长时间的“诗歌阶段”之后,进入“散文时期”的,他的散文,以自己离开故乡前的十四年生活为母题,将之前未纳入诗歌创作的童年、故土、自然、乡邻、父亲、母亲等早期生命体验融进童年回忆——降生在厚厚的“绵绵土”上,成长在滹沱河上游的苦寒之地,心底里流淌出深沉的生命之歌,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情。 本书精选牛汉散文60余篇,包括童年名篇《绵绵土》《打枣的季节》《月夜和风筝》《海琴》《父亲,树林和鸟》等;怀人佳作《一颗不灭的诗星》《荆棘和血液》等,以及散文漫谈《诗和散文都是我的命》《谈谈我的土气》等。配以作者不同时期照片二十余幅,图文并茂,给读者丰富的阅读体验。
牛汉散文 目录
【目录】
导读
绵绵土
*初的记忆
骡王爷
——童年牧歌一章
去摘金针菜的路上
上学**天和墨刺的梅花点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
——追念死去的**个朋友
我的脚与砍山鞋
灯笼红
祖母的呼唤
我的**本书
**次绘画创作
打枣的季节
吃蚂蚁
玉米浆饼
心灵的呼吸
月夜和风筝
阳婆和月明爷
——祖母讲的神话
海琴
塑造梦的泥土
喂养小雀儿
宝大娘
掏甜根苗
苦香的,柳笛声声
扫霁人儿
早熟的枣子
少年与萤火虫
——父亲对我讲的童话
父亲,树林和鸟
迷人的转蓬
秃手伯
活着的伤疤
母亲的**次人生经历
一斗绿豆
滹沱河和我
一窠八哥的谜
接羔
活吞小鱼仔的悲剧
送牢饭和公鸡打鸣
——童年牧歌之一
高粱情
离别故乡
我的祖先和一把剑的传说
含羞草的冤屈
水仙的晚年
我和小白
童心
重逢**篇:路翎
以心灵关怀心灵
——忆雪峰和吕荧的*后一段友情
漫说老聂
一颗不灭的诗星
——痛悼尊师艾青
一个不相信死的人
——记与萧军*后一次见面
诗人天蓝骑马去了
诗和苏金伞和我
一个钟情的人
——曾卓和他的诗
荆棘和血液
——谈绿原的诗
散文这个鬼
诗和散文都是我的命
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
谈谈我的土气
我是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
诗的新生代
——读稿随想
关于文字与创作的关系
——与郑敏的通信
我仍在苦苦跋涉
牛汉散文 节选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牛汉《绵绵土》 很小的时候,看到祖母和母亲打枣,千百颗枣子从她们身上朝四面八方溅射着,映着秋天浓艳的阳光,那种梦境般的情景,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光芒四射的红枣坠落下来,从祖母和母亲身上溅射出去,祖母和母亲变成了两个能发光的神话里的人物。 ——牛汉《打枣的季节》 滹沱河是我的本命河,它大,我小,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但是,我又能把它深深地藏在心里,包括它那深褐色的像蠕动的大地似的河水,那颤栗不安的岸,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和气氛。几十年来,每当濒于绝望时,我常常被它的呼吼声惊醒过来。 ——牛汉《滹沱河和我》 我们家乡有一种香瓜叫做“灯笼红”。这瓜熟透了以后,瓤儿红得像点亮的灯笼。我的曾祖母就像熟透了的灯笼红。她面孔黧黑,布满老树皮般的皱纹,可是心灵却如瓜瓤那么又红又甜。我的童年时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老人,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生,*后在生命的内部酿出并积聚起隽永而仁慈的美好性灵。 ——牛汉《灯笼红》 在一篇文章里,我说过“鼻子有记忆”的话,现在仍确信无疑。我还认为耳朵也能记忆,具体说,耳朵深深的洞穴里,天然地贮存着许多经久不灭的声音。这些声音,似乎不是心灵的忆念,更不是什么幻听,它是直接从耳朵秘密的深处飘响出来的,就像幽谷的峰峦缝隙处渗出的一丝一滴叮咚作响的水,这水珠或水线永不枯竭,常常就是一条河的源头。耳朵幽深的洞穴是童年牧歌的一个源头。 ——牛汉《灯笼红》 童年时,我没有见过海,但我从海琴声中听到了大海美妙的旋律。后来,我见到大海,大海的涛声当然比海琴的声音要雄浑得多,但是它并不能代替我童年的海琴,即使是交响乐,也淹没不了海琴声音: ——牛汉《海琴》 泥土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我从泥土学到心灵的语言,它的辞语是奇特的,充满了激情和幻梦。 ——牛汉《塑造梦的泥土》 挖下的土不是散的,酥的,是成片成片的,像花瓣儿似的会卷了起来。我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真的,不但像花,闻一闻还有些沁人心脾的奶汁的气味。以后,我隔几天悄悄来挖一次。这种土,质地为什么这样的奇特,大概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否则为什么能透出光彩,还有着天然的可塑性?人还没有去用它去雕塑什么,它自己已快活地绽成一片片花瓣。 ——牛汉《塑造梦的泥土》 我当年在家乡做梦似的捏弄出那么多的泥东西,得到同伴们的喜爱,绝不是由于我的心灵手巧,而是因为那方土脉本身有灵气,那片古老的纯净的黄土地渴望着把自身塑成*美的生命。 ——牛汉《塑造梦的泥土》 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身上多半带着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疤。如果伤在手上脸上,谁都看得见,而有些伤是很难看见的;首先,他就不愿让谁看见,而有些伤,即使让你看,你也看不见。这些伤,痛在骨头里,深深地藏在倔强而沉默的心灵里,只能从他们艰难的步态(并非由于衰老,他们大都不过三十几岁的人)和深重的哮喘声中,猜想到他们曾经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病痛,小灾小病难不倒他们。 ——牛汉《秃手伯》 绵绵土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悲壮*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滹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棱棱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打枣的季节 麦熟一晌,从收割到净场,不过三五天工夫。打枣也有个季节,记得是在农历的八月中旬,也不过三五天,全村的枣树差不多就打光了。打枣多半是在半前晌,多由女人和娃娃们操持和尽情享受;是的,打枣确是一种使心灵快活的享受,可惜一年只能有一回。那几天,整个村庄此起彼落地爆响着一阵阵的欢腾声:先听到成千的枣子在地上蹦蹦跳跳的声音,接着就响起了孩子们噢噢的欢呼。熟透的红枣,在阳光的照耀下,忽闪忽闪地瀑布般溅落下来,在院子里滚来滚去,总有那么几颗跑到谁也难以找到的角落躲起来。打枣捡枣都十分有趣。 我家有两个院子,地势高的上头院有四棵枣树,下头院只有一棵。下头院的一棵不大结枣,它弯腰驼背,老态龙钟,有半边树干没有皮。下头院早年有个牲口圈,曾祖父在世时,我家还趁一套大车和一匹骡子。这棵枣树的皮就是被那匹骡子蹭痒蹭掉的,这是曾祖母对我说的。这棵伤残的枣树没有人管,枣子刚见点红圈儿,就被孩子们摘去大半,实际上扔的比吃的多。我不吃这棵树的枣子,我总是摘上头院挨门的那棵树的枣子,它汁多,核小,又大又甜。我们家收枣,实际上只有两棵树上有枣可打,一棵在羊圈的门口,一棵紧靠父母住的房子。这两棵树的枣子我和弟妹们都不大敢摘。 打枣前个把月,已经摘过一回,是由我攀到树上一颗颗地摘的。拣个儿大五六成熟的,满满地摘一大篮子。母亲把它们洗净装在瓷罐里做醉枣。村里做醉枣的人家不是很多。醉枣的坛子严严地封着,搁在父母房里的条桌上,开坛的一瞬间,孩子们都屏着气团团围着母亲,坛盖一开,一股浓烈的酒香枣香喷发了出来,正在院子里的祖母立刻便可闻到,笑笑说:“醉得正合适。”要是醉得酒味压倒了枣味,就不算合适。开坛时,醉枣的香气隔几家院子都能闻到,仿佛绽开了一朵奇异的香喷喷的仙花。开坛的当天,金祥大娘照例来我家要一碗醉枣,回去给当屠夫的大伯下酒。我家收枣时节,父亲从不插手,宁神静气地在屋里看他的书,炕桌上摆一碟刚刚出坛的红艳艳的胖胖的醉枣。看几页书,吃一颗醉枣。 打枣的事由我祖母主持,先命令我把整个院子扫净,一粒羊粪蛋都不能留。打枣前,我早已高举竹竿,威风凛凛站在树下听候发令。祖母再三叮咛我,切不可使劲太大,下手要轻。当枣子噗拉拉坠落,击打在我的头上、肩头上、手臂上,不但不感到疼,还有一种酥痒的快感。而且凡是落在人身上的枣子,弹跳得格外远。很小的时候,看到祖母和母亲打枣,千百颗枣子从她们身上朝四面八方溅射着,映着秋天浓艳的阳光,那种梦境般的情景,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光芒四射的红枣坠落下来,从祖母和母亲身上溅射出去,祖母和母亲变成了两个能发光的神话里的人物。如果我四十多年前把画学成,早已把这情景画了出来。 我自小认为,我的祖母是个内心灵秀的女人,她常常说出一些极有诗意的话。打枣时,她似乎诗兴大发,说,“树上的枣子不能打得一干二净,要留十颗八颗。到下雪时,这几颗留下的枣子会出奇的红,出奇的透亮。”祖母指着树尖上的那几颗晶红的枣,又说,“一来看着喜气,二来冰天雪地时,为守村的鸟雀度饥荒。”老人们说,一个村子,总会有几只不愿飞走,忍饥挨饿死守着村子过冬的鸟雀。树上的枣很难打尽,树梢的枣大都是后结的“老生子”,*后的果实往往不会成熟,枣树总是格外地护着它们,有时使着劲儿打,它们像焊在树枝上一样牢固。祖母对我说:“老生子不能打,再打,枣树会生气,明年不结枣子,或者结出来的也是苦的。” 打枣,不但女人和娃娃们快活,枣树何尝不快活!听到枣子溅落到地的声音,光芒四射地从树身上飞溅出去,晶亮如飞虹,那情景,那声音,那光彩,枣树能不感到快活吗?祖母深信不疑,我也信。 灯笼红 我们家乡有一种香瓜叫做“灯笼红”。这瓜熟透了以后,瓤儿红得像点亮的灯笼。我的曾祖母就像熟透了的灯笼红。她面孔黧黑,布满老树皮般的皱纹,可是心灵却如瓜瓤那么又红又甜。我的童年时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老人,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生,*后在生命的内部酿出并积聚起隽永而仁慈的美好性灵。 曾祖母至少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四岁那年,她无疾而终。我跟她在一盘大炕上挨着睡,她死的那天晚上,把我的被褥铺好,像往常那样,如打坐的僧人,久久不动地盘腿坐在上面,为的是把被窝焐得暖暖和和的。我光身子一出溜钻进被窝,曾祖母隔着被子抚拍我好半天,直到入睡为止。那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当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梦的时候,曾祖母在我身边平静地向人生告别了。 我睡得死,醒来时天大亮。平时曾祖母早已起床下地,坐在圈椅里跟祖母说话,今天为甚仍稳睡着?侧脸一瞧,一双绣花的新鞋露在曾祖母的被头外面,不是过大年,为甚穿新鞋?还有,她怎么头朝里睡?我愣怔地坐起来,看见姐姐立在门口嘤嘤地哭泣,屋里有几个大人靠躺柜立着。我坐起来。刚喊了声“老娘娘”(家乡对曾祖母这么叫,**个“娘”读入声),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连被窝一块抱走,送到父母住的屋子里。我哭着,我并不晓得曾祖母已死,喊着“老娘娘……”这时我才听见我的几个姐妹也都哭喊着“老娘娘”。 我家的大门口平放着一扇废弃的石磨,夏日黄昏,曾祖母常常坐在上面。我从远远的街角一露面,她就可着嗓门喊我:“汉子,汉子,快过来!”我们家乡女人把丈夫才叫“汉子”。曾祖母“汉子汉子”的叫我,引得过路的人狂笑不止。这个细节一直没有忘记。我跑到她身边,她牵着我的手走进大门。一进大门,有一间堆放麦秸的没门没窗的房子,麦秸经过碌碡压过以后很柔软,我们叫“麦滑”。当年的麦秸都有股浓馥的太阳味儿,我自小觉得凡太阳晒过的东西都有一股暖暖的甜味儿。在收割季节的庄稼叶子上能闻到,地里的土坷垃上能闻到,熟透的“灯笼红”香瓜散发出的太阳味儿*浓。 曾祖母叮咛我:“你看着,不要让人来。”我心里全明白,假装着懵懵懂懂,隔着麦秸,我早闻到了诱人的灯笼红的香味。曾祖母跪在麦秸上,双手往里掏,掏得很深,半个身子几乎埋进麦秸里,麦秸里沉聚的芬芳的太阳味儿被扬了起来,刺得鼻孔直痒痒。她终于掏出三五个“灯笼红”,逐个闻一闻,挑出其中*熟的一个递给我,把剩下那几个又深深地寄在麦秸里面。家乡话中的“寄”是藏匿的意思。甜瓜寄在麦秸里两三天,能把半熟的瓜酿得全熟,浓浓的香味溢出了瓜皮。香味正如同灯放射出的光芒,只不过不像灯光能看得见。其实跟看得见也差不多,一闻到香味就等于看见红烁烁的瓜瓤了。我们回到大门口磨盘上坐着,曾祖母眼瞅着我一口口地把瓜吃完。 我连曾祖母的姓和名字都不知道。她留给我的只有上面说的一些梦一般的事迹。隐约地记得她个子很矮小,穿的袄肥而长,宽大的袖口卷起半尺来高,里面总寄放些小东西,她会从里面给我掏出几个醉枣或麦芽糖。对曾祖母的手我还有记忆。她总用干涩的手抚摸我的面孔,晚上当我钻进被窝,她的手伸进被窝久久地缓慢地抚摸着我,从胸口直抚摸到脚心,口里念念有辞:“长啊,长啊!”我现在仍能隐隐感触到她的手微微颤动着,在我的生命的里里外外……别的,关于她,我什么也记不得了。她早已隐没进了无法忆念的像大地一般深厚的历史的内腔之中了。 听说曾祖母年轻时性子很刚烈,说一不二,村里有个姓王的武举人(是全县有名的摔跤场的评判),都怕她三分。到了晚年,她却异常的温厚,像收完了庄稼的一块田地,安静地等着大雪深深地封盖住它。她从人世间隐没了,回归到了生养她的浑然无觉的大自然。大自然因他们(无以数计)生命的灵秀和甜美而更加富有生育的能力。 月夜和风筝 在我童稚的心里,父亲很深沉,与父亲的生命能以融合的月夜和风筝也很深沉。深沉,意味着识不透底蕴。对于月夜和风筝,父亲有许多自己的哲学和具有哲理的玄想。他当年不到三十岁,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大革命,人显得有点苍老。我正在童年,对父亲困惑不解。经过五六十年心灵的反刍,现在才渐渐地有些理解了:父亲当时精神上很困厄,活得不舒展。 父亲从来不在白天放风筝。祖母说他的风筝是属蝙蝠的。父亲说:“白天不需要风筝,白白亮亮的天空,要风筝干什么?”父亲总是当天地黑透了之后才去放风筝。奇怪的是,白天没有风,黄昏以后,常常不知不觉地来了微风,似乎不是从别处刮来的,风就藏在我们村子里一个角落,它觉得应该醒了,站直身子,轻飘飘地跑起来。有时候,白天风刮得很狂,一到黄昏便安生些,仿佛事先与父亲和风筝有过默契。 放风筝在春二月,天日渐长起来。天暗下来时,不用父亲唤我,我会跟在他后面,帮着把风筝从我家的东屋弄出来。丈把高的人形的“天官”风筝由父亲自己扛,我用双臂抱着放风筝的麻绳,缠得很紧,足有西瓜那么大那么沉。父亲悠然地看看天,说:“又是个月明的天!”只有我知道,他并不是赞美月夜,他希望的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黑夜,“没有月亮多好。”父亲慨叹一声。实际上黑透了的夜极少。我对父亲说:“有月亮放风筝才好。”我想,天黑会闷人,有月亮能看见升天的风筝,看见红灯笼与星星在一块闪烁,还能望见海琴振颤的翅羽。父亲不答理我。到得街上,他说:“没有月亮和星星,天是囫囵的,完完整整的。”“为什么?”我问。父亲回答:“天黑透了,天才能安静下来,风筝在天上才自在。天空只有风筝和灯,只有海琴的歌,一个完美的世界。”父亲像是在吟诗。我当时还是喜欢在月明的夜放风筝,我喜欢望着朦胧的天,它越看越深,越看越高,风筝飘带上的月光跳来跳去,还能看见变化莫测的飞云。红灯摇摇晃晃,比所有的星星快活得多。如果天全是黑的,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天也看不见我们。父亲摇摇头不作解释,他清楚他那套玄想无法让我理解,而我也有我自己童稚的玄想。 父亲年轻时喜欢写诗、吹箫。他有时自言自语,以为我听不懂,听到我的某一句问话以后,他惊愕地回过头来望一望我,似乎我不应该听懂他的话。 总有一群小孩跟在我们后面吵吵嚷嚷,如果我和父亲不放风筝,这些孩子都不会到街上来,家里老人不放心他们在月亮地里跑动。我和父亲照例在一个小的广场上停下来。这里实际上是村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没有车马,就成为一处注满月光的开阔的地方。靠北边,有个高坡,父亲站在上头就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不需要助跑,他让我把风筝直立在丈把远的地方,在背后扶着风筝。父亲高高扬起双臂,猛地向上一拽,风筝抖动一下,被惊吓得跳起来。父亲手中的绳子一抖一拽地就把风筝逗到了空中。风筝显得很高兴,它和父亲配合得很好。一会儿风筝就升高了。风吹着,月光抚摩着“天官”的彩衣,发出瑟瑟的声音。 一到春天,村里的枣树上,总有风筝挂在树上,都是孩子们的瓦片风筝,父亲的风筝从来没有挂在树上过。我们村家家院子里,多半有几棵枣树,枣树是长不高的,风筝很容易就能越过。等到风筝放得很高以后,父亲横着身子一步一步地移到五道庙前。五道庙有结实的栅栏,父亲把绳子放尽,手里只剩下一根光滑的木棒,他把木棒横别在栅栏上。 五道庙前是个热闹的人场,这时父亲掏出烟锅,抽着后,就坐进人群里去,似乎风筝跟他无关了。这时我感到风筝只归我所有了。我担心天上风大,风筝会倒栽下来。我不时用手摸摸绳子,如果绳子绷得太紧,发出嘎吱的声响,我就对父亲说,“绳子怕要断。”“没事。”父亲对我说,“你快回去把灯笼和海琴拿来。” 这时才是我*高兴的时刻。我跑得飞快,幸亏有月亮,看得清路,身后跟着一串孩子,仿佛我是风筝,身后的一长串孩子是风筝的飘带。“成汉哥,今天的海琴让我拿!”“成汉哥,灯笼由我拿!” 父亲的海琴和灯笼搁在东房的供桌上,蜡,我得向祖母要,蜡不能随便放,搁在供桌上,一会儿就会被老鼠吃光。我和孩子们又是一阵小跑,我当然地跑在前头,同伴们有的拿蜡,有的提灯笼。海琴由我拿,我从不让别人碰的。 父亲站起来,用手摸摸风筝的绳子,如果绳子绷得不够紧,海琴常常放不上去。父亲放海琴和灯笼不让别人插手,他先把海琴联到绳子上,再把灯笼挂在海琴下边。他总是当风筝稳定到*佳状态时,才小心地把灯笼点亮。我和孩子们鸦雀无声,等待着海琴和灯笼开始升起的一刹那,父亲异常专心,眼睛也明亮起来,不住地看天、看灯笼和海琴,只听孩子们一声喊:“海琴动了,动了!”海琴在一片欢呼声中沿着琴弦似的绳索嗡嗡地歌唱着升了上去,越升越快。我把耳朵贴着绳子谛听,真能听到远方大海的声音,嘿,大海的声音原来像一群蜜蜂在飞。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海琴和灯笼升到风筝那里。 天空出现了一颗与众不同的红色的星,摇摇晃晃的星,会歌唱的星。灯,在天空,也不过亮半个钟头。灯灭了以后,放风筝的高潮便结束。孩子们纷纷回家。我仍忠实地守望着天上的风筝。失去灯,风筝看去更明显些,它摇曳着,隐约能听到飘带扑瑟瑟的声音。灯笼和海琴也像我一样陪伴着风筝,还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直等到半夜,父亲和广场上的人都立起身来,父亲才和几个大人把风筝收了下来。如果大人们的“自乐班”还忘我地吹奏响器,何时收场就难说了。风筝在天上多半很安生,只有几次,忽然起风,父亲提早收下风筝来。风筝靠墙立着,我守着它,还守着灯笼和海琴。大人们仍吹吹打打,不愿散场。 父亲年年都要放风筝。每年都认真地把风筝修补一番,重新染一次颜色。村里放风筝的人有好多家,都没有我父亲放风筝那样虔诚和认真。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流行一个谚语:“史桂林的风筝头一份儿。”卖豆腐的老汉夸自己的豆腐说:“我的豆腐是史桂林的风筝。”父亲的风筝挂上灯笼之后,三五里内的几个村庄都看得见。 这放风筝的一套技能父亲是怎么学来的,可能是我们家乡自古传下来的,也可能是他从北京城学来的。但是,我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见过有人夜里放风筝,更没见过挂海琴和灯笼的风筝,真感到奇怪和遗憾。 父亲为什么总在月明的夜放风筝,而且特别喜欢在黑夜挂灯笼和海琴,我此刻真有点理解了。如果我现在放风筝,我也一定在黑夜放,而且一定挂上灯笼和海琴。 当风筝放稳了之后,父亲就不停地抽烟,很少跟谁说话,他仿佛很深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放风筝跟他吹箫的神情很相近。他有自己放风筝的哲学,希望风筝带着灯笼的光亮和海琴的歌,也带着他的心灵,升向高高的空旷的夜空。 后来,到了四十年代,我知道,父亲在家乡那些年写过不少的诗,有旧诗,也有新诗,从来没有发表过,他似乎没有想到过要发表。 还有,父亲一生嗜酒。他放风筝之前,喜欢先喝点我祖母酿的黄酒。我们家乡的春二月,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夜间是很冷的,有月光的夜更加清冷清冷。 似乎一旦风筝连同海琴和灯笼升到天上,月夜就变得温暖起来。至少我父亲的感觉是这样。
牛汉散文 作者简介
牛汉 (1923—2013) 原名史成汉,又名牛汀,蒙古族,山西定襄县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1940年开始文学创作,以诗闻名,同时也是散文大家。已出版诗集、散文集二十余本。诗集《温泉》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历任《中国》执行副主编、《新文学史料》主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近年来在日本、韩国、马其顿等国出版了诗歌选集。
- >
巴金-再思录
巴金-再思录
¥14.7¥46.0 - >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24.4¥49.8 - >
史学评论
史学评论
¥22.7¥42.0 - >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新文学天穹两巨星--鲁迅与胡适/红烛学术丛书(红烛学术丛书)
¥9.9¥23.0 - >
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自编集
苦雨斋序跋文-周作人自编集
¥5.8¥16.0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9.3¥19.0 - >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小考拉的故事-套装共3册
¥36.7¥68.0 - >
随园食单
随园食单
¥15.4¥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