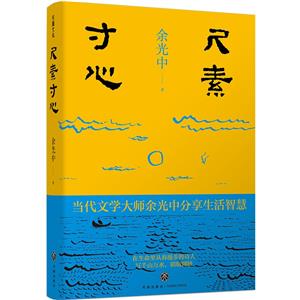-
>
野菊花
-
>
我的父亲母亲 - 民国大家笔下的父母
-
>
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965-1966
-
>
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1959-1960
-
>
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1957-1958
-
>
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
-
>
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1949-1953
尺素寸心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5571011
- 条形码:9787545571011 ; 978-7-5455-7101-1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尺素寸心 本书特色
1. 作者余光中因一首《乡愁》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其散文创作同样具有很大影响力,被誉为“文坛璀璨的五彩笔”、“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在大陆、香港和台湾都拥有较大读者群。 2. 从大陆到港台,从中国到欧美,余光中的一生都在漂泊,却认定大陆永远是自己的母亲,他的文字时刻都能引起游子的共鸣。 3. 作者学贯中西,是永远的华语文学大师,他的散文写尽一代人的乡愁、记忆与青春,传递跨越半个世纪的纯粹与感动。
尺素寸心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名篇合辑,精选了作者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如《思台北,念台北》《凭一张地图》等。本书以“故乡”与“旅行”为主题,包括乡愁记忆、游记见闻等内容。书中有壮阔铿锵的大手笔,有细腻柔绵的小写意,还有深沉真挚的情感和思考,以及深厚的人文情怀。读者阅读此书可以进一步了解作者的内心,感受大师丰富的精神世界。
尺素寸心 目录
**章 乡愁绵绵,莫问归期
万里长城
思台北,念台北
从母亲到外遇
思蜀
新大陆,旧大陆
第二章 故国千里,乡关何处
山盟
沙田山居
关山无月
水乡招魂——记汨罗江现场祭屈
片瓦渡海
清明七日行
故国神游
第三章 彼岸风景,诗意远方
石城之行
南半球的冬天
从西岸到东岸——第四度旅美追记
凭一张地图
海缘
山国雪乡
红与黑——巴塞隆纳看斗牛
第四章 万物可期,人间值得
地图
听听那冷雨
尺素寸心
娓娓与喋喋
粉丝与知音
尺素寸心 节选
《新大陆,旧大陆》 1 自从一九四九年七月的一个夏日,我在厦门的码头随母亲登上去香港的轮船,此生就注定了半世纪之久不再见大陆。当时年少,更非先知,怎料得到这一走,早年的大陆岁月就划然终止了。怎料得到,抗战的长魇也不过八年 就还乡了,而这次流离,竟然“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怎料得到,当时回顾船尾,落到茫茫的水平线后的,不仅是一屿鼓浪,而是厚载一切的神州。更未料到,从此载我荫我,像诺亚方舟的,是一座灵山仙岛。 但是不幸中隐藏着幸运,当日那黑发少年已经二十一岁了,汉魂已深,唐命已牢,任你如何“去中国化”都摇撼不了。所以日后记忆之库藏,不,乡思之矿产,可以一凿再凿,采之不尽。丹田自有一个小千世界(microcosm),齐备于我。如果当时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甚或更小的孩童,则耿耿乡心,积薄蕴浅,日后怎么禁得起弥天的欧风美雨? 在妈祖庇佑的蓬莱米岛上一住八年,从台大的插班生变成师大的讲师,从文艺青年变成文坛新秀,从表兄变成男友、新郎然后是父亲,那时并不很怀念大陆,反觉得那一片空阔愈来愈陌生,那陌生的社会正取代了我熟悉的童年。 旧大陆的种种像因缘未了的前世,不续不断,藏在内脏的深处像内伤隐隐,隐隐未发。这么内耗兼偏安,到我三十岁那年,母亲死了,旧大陆似乎更远了。而几乎是同时,珊珊生了,她响亮的啼声似乎是一个新时代在叩门,铜环铿铿。也几乎是同时,新大陆在西半球召我。 2 三去美国,**次读书,只留一年,后两次教书,各留两年。那时有志青年的正途正是留学,所谓镀金。我一年修得硕士,就迫不及待,匆匆回到岛上,只能算是镀银。我匆匆回来,为了还没有克服丧母之痛,为了丢不下还是新娘的妻子,而新生的女婴还没有抱够,甚至看清。 **次旅美,我目眩于花旗帝国之新奇富丽,却心怀故国与故岛。 我的乡愁真正转深,在山河的阻隔之上,更与同胞、历史、文化绸缪难解,套牢成一个情意纠结,一个不肯收口的伤口,是在第二次旅美之后。文化充军、语言易境、昼夜颠倒、寒暑悬殊,使我在失去大陆之后更失去孤岛,陷于双重的流离。唯一能依靠甚至主宰的,只剩下中文了。只剩下中文永不缴械,可仗以自卫、驱魔、召魂。 美国的经验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又不尽然。我出身于外文系,对西方后来居上的**强国当然不无了解,更不无向往。那时我们读的英文其实是美语,对当代西方生活的印象也大半来自好莱坞。不过我在去美国之前早已读过不少美国文学,甚至为台北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译过五十多首美国诗,而我*早出版的两本中译小说:《老人和大海》《梵谷传》 ,也都是美国作家所写。 第二次去美国,教书的负担不算很重,而待遇又不薄,更值壮年,体能正当巅峰,自信臻于饱满。为了认识新大陆,做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我决定学驾驶,并且用三分之一的年薪买了一辆新车。从此美国之大,高速路之长,东岸与西岸之远,都可以应召而来,绕着我的方向盘旋转。我似乎驰入了惠特曼豪放的新史诗里,一目十行,纵览美利坚魁伟的体魄,汇入了**世界的荡荡主流。 那当然只是方向盘后*初的幻觉。从大西洋浒到太平洋岸,四轮无阻,纵然踹遍了二十四州,也不过是被吸入了美利坚抖擞的节奏,随俗流转。高速的康庄大道无远弗届,但没有一条能接到长安。时速七十英里 ,纵使将芝城旋成急转的陀螺,也无法抖落岁月的寂寞。四轮之上的逍遥游,不过是一场睁眼的梦游。那几年,尤其当家人尚未越洋去相会,这一缕郁郁的汉魂,深切体认了寂寞的意义:绝对的自由,彻底的寂寞。第三次再去火鸡帝国,不但寂寞,而且孤高。命运把我的棋子下在西部的首都,城高一英里的丹佛,所谓Mile-High City 。不过这一次我不再逍遥梦游了,只孤悬在落矶峰群 的山影里,两年悠悠的岁月像一程延长的重九登高,但用以辟邪的不是茱萸和菊酒,而是,你再也想不到吧,西部的民谣、乡村歌曲、灵歌、蓝调、摇滚乐。 其实也不是辟邪,而是抵抗寂寞。**次赴美,我修读的是现代艺术,但认真聆听的是古典音乐,从拉摩听到拉罗,从格希文听到拉赫曼尼诺夫, 其实大半都不算美国音乐,而现代艺术的大师也轮不到美国人。我只是站在美国的窗口,遥窥欧洲罢了。 第二次旅美那两年,正当四披头席卷西方,狄伦也崛起于美国, 我却仍奉古典音乐的正统,浑不知美国青年侧耳倾心的是另一种节奏,和众而又曲高。第三次才轮到我,一个迟到的周郎,来侧耳听赏。于是从却克·贝瑞到艾丽莎·富兰克林,从琼·拜丝到玖妮·米巧,从汉克·威廉姆斯到唐诺文到亚尔伯乐,我买了近百张的此类唱片。 至于四披头的唱片,包括那张封套对折的《花椒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乐队》 ,我更是搜罗齐全。美国知识青年厌弃正统的美国生活格调,有意“去美国化”,而且拔去“黄蜂”(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的毒刺,所发展出来的嬉皮文化甚至反文化,要在这些江湖乐手的琴音歌韵里才能领会。 这种通俗而不庸俗的江湖风格,对我颇有启发,令我认真思考,摇滚乐何以热而现代诗何以冷,并且领悟,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不妨浅出。一九七一年我回到台湾,一气呵成的那几首民谣风的短歌:《乡愁》《乡愁四韵》《民歌》《民歌手》,后来果然入乐成曲,汇成了民歌运动,助长了校园歌曲,都是由美国黄蜂社会的此一另类文化所触发、转化而来。 3 第三次旅美后回到台湾,此生的“美国时代”就结束了。后来虽然又多次访美,但内心的波动已远不如前,自知新大陆的缘分已尽。一九七四年举家迁去香港,本以为可以近窥大陆,多了解一点日渐陌生的母亲,却没有想到,从此竟开启了去欧洲之门,得以亲近另一个旧大陆,西方的大陆。原本要用香港做北望的看台,不期更进一步,竟找到了西游的跳板。 **次去英国,是从纽约起飞,伦敦入境的。这样的行程正象征倒溯的怀古。其实当初我去新大陆,也是从西雅图入境,然后是中西部,*后才是东岸。就怀古之旅而言,那渐入渐深的心情真可谓倒啖甘蔗。 美国东岸的地名,以“新”开头的不少,大家习以为常,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原名是指何处了。纽约人里有多少说得出“约克”在哪里呢?换了是纽罕布什尔、纽泽西, 恐怕也一样。我住惯了美国中西部,初去新英格兰,就处处觉得古旧。在那一带驾车,加油站的工人竟然对我说:Yes,governor !这“化石口语”据说在今日的英国仍然通用,当时我却受宠若惊,幻觉是走进了旧小说里,听人称我一声“官人”。 这种古腔英国人也会带来东方。香港的“收银处”,中文已经古色古香了,但其旁的shroff 就更加冷僻,连在大字典里都查不到,美国人当然更不认得。 到了伦敦,才会觉得美国有多新,多大,多嚣张。英国的计程车是端庄的方轩,司机更像稳健的老绅士,谈吐斯文。泰晤士河边的国会大厦堂皇而不失庄重,那不倒翁的大笨钟阅世太深,钟面上却看不出多少感慨。只有朱红色的双层巴士满街游行,为迟暮而矜持的帝国古都带来童话的稚气。唐宁街十号该是全世界*不起眼的首相府了,跟白金汉宫的排场怎么相比?英国官署所在的White Hall 似乎迄无定译,不知该叫白厅、白堂或白衙。没有人不知道华府有个白宫,但敢说很少人知道伦敦有个白衙。 中文把美国的总统府译成“白宫”,歪打正着,恰中洋鸡的下怀。美国人尽管标榜民主,潜意识深处仍以帝国自命,但是总不好意思在波多马克河岸建一座皇宫,也不便在落矶山上盖一座古堡。其实,他们把甘乃迪与贾桂林是当做金童玉女的帝后来移情的。 不过英国毕竟不算正宗的欧洲。直到一九七八年,我五十岁时,走在香热里榭 的街头,甚至登临凯旋门上,才真有实践欧土的感觉。如果伦敦是美国人的阁楼,藏着祖父的日记,巴黎就是欧洲人的阳台,可览邻居的花园。巴黎的成功在于包容拔萃,说它是欧洲首府也许还有争议,但是当欧洲的艺都应该同然。梵谷、毕卡索、夏高、莫地里安尼、史特拉文斯基从各国蜂拥来朝圣,肖邦、王尔德、邓肯、布朗库西殊途同归,都来此安息。 欧洲之子爱伦坡没有死在巴黎,太可惜了,幸好他终于复活在法国。 凡坐船进纽约港的人,都会仰见矗立的自由女神,一手握着法典,一手高举着火炬,欢迎前来投奔的移民。那景象太有名了,简直成了美国的店招,却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设计人也是法国雕塑家巴尔托地 。这是法国精神启发美国的*显赫地标,但其光芒却遮蔽了同一造型的雕塑,许多游客竟然不知道还另有一座,具体而微,竖立在塞纳河上,格禾纳尔桥 畔的一个岛上,正是美国人所回赠。 从初践欧土迄今,我去过的欧洲国家已有十七,约为我周游列国之半;加起来旅欧的时间只有六个月,但启发颇多。于此十七国中,所见当然有深有浅,浅的像卢森堡,只有一夕,他如丹麦与匈牙利,各仅两晚;至于意大利,只到了科摩与米兰,是从瑞士入境,当晚就回露加诺了。 比较深的是西欧的大国,依次是英、法、德、西。我在这四个国家都开过车,也搭过火车。在英国与德国且开过长途;尤其是在德国,从北到南,自波罗的海畔一直到波定湖 边,纵贯了日耳曼的全长,不但路况完美,秩序井然,而且高速无限,真不愧飙车的“乌托邦”(Autobahn)。德国人在我所见的欧洲人中,是*爱整洁、*守秩序、*为勤奋的民族,一大清早日耳曼人就浩浩荡荡,在街上健步来去了。西班牙人正相反,不但早上人少,而且午休很长,晚餐要拖到九点以后,生活节奏一贯的悠悠缓缓,只有斗牛和跳佛拉曼戈 时才使出劲来。 南欧与北欧之分,全凭阿尔卑斯山系,再加上比利牛斯一脉吧。瑞士恰在分水脊上,南下的火车入隧道之前,轮踩的还是德语地区,一出隧道,咦,怎么竟闯进意大利语区了呢?德国跟西班牙的对照,也正是北欧与南欧,新教与旧教,矜持与朗爽,日耳曼子音切磋与拉丁文母音圆融的互异。至于法国,则介乎其间,难以归属南北,只能视为西欧。英国更其如此,还带一点偏北。 相对于西欧,东欧从哪里开始呢?德国以东应该就算东欧了,不但由于地理方位,更因波兰、捷克、匈牙利与巴尔干各国多用斯拉夫语,对西欧说来显已非我族类了。我去欧洲二十多年间,前半期多游西欧,后半期也去了东欧,包括匈牙利与捷克,而波兰与俄罗斯甚至各游了两次,对这些国家认识更深。 九十年代初,匈牙利开而不放,观光条件仍差,服务态度生硬而冷漠,但是多瑙河中分的布达佩斯却难掩国色,临流自鉴,明艳十分动人。一条斜行的大街以阿提拉(Atilla)命名,而匈牙利人姓在名前,也令我感到惊喜。至于布拉格,早已敞向西欧甚至全世界了,没有旅客会不喜欢。年轻俊美的海关官员竟然会和旅客开玩笑,反比美国的海关可亲。 在布拉格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一位小学生竟然让座给我。这种礼貌在“自由世界”也很罕见。华沙的街头,汽车也非常有礼,常常慢下来,甚至停下来,让行人过街。莫斯科的麦当劳速食店根本不播音乐,街边确有乞丐,但那些老妪的衣衫都朴素而整洁,只静静坐着,脚边放着空盘,并不追缠游客。满街都是纤修高挑的丽人,轻灵的步态似乎踏着天鹅湖而来,至于小孩子,几乎找不到一个不好看的。 在圣彼得堡,一位俄国教授请我们去他家做客。狭窄的客厅里临时搭起一张餐桌,主客六人必须在迫挤的沙发、书架与钢琴之间绕道而过。那是二〇〇〇年初夏,俄国正苦于粮荒,许多人都被迫上山去采菇充饥了,主人却罄其所有,做了美味的肥菇与鱼汤飨客,我们嚼着、咽着,感动而又不安。想到普希金与托尔斯泰的子孙还有人正蹲在街角行乞,我几度要掉下泪来。 二次大战以后,英语与美国文化逐渐风行;所谓英语,其实是美语,这方面的全球化早已开始了。五十年来,台湾接受西方的影响,主要以美国为门户,其实美国文化只是西方文化的下游。我去欧洲,乃是溯其上源,正如爱伦坡所喟叹的:“回到希腊不再的光彩,和罗马已逝的盛况。”然而迄今我始终无缘去两地:原本计划好的亚波罗神庙 之旅,和威尼斯海上之行,先是阻于波斯湾的交兵,继又挫于南斯拉夫的内战。 4 另一个旧大陆,近十年来却不断召我回去,不是回希腊与罗马,而是回去汉唐。我曾戏言:“欧洲是外遇”,然则回到自己的旧大陆,该是探亲,不,省亲了。 自从一九九二年接受北京社科院的邀请初回大陆以来,我已经回去过十五次了,近三年来尤其频密。例如南京,我的出生地,也是我读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古城,三年内我就回去了四次,*近的一次是今年五月,去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像我这样在两岸三校(南大、厦大、台大)都是校友的人,恐怕很少了。这样的“圣三位一体”隐喻了我身逢战乱的少年沧桑,滋味本来是苦涩的,不料老来古币忽然变成现金,竟然平添出许多温馨的缘分。在南大校庆的演讲会上,我追述这一程夙缘,把“挤挤一堂”的热切听众称为“我隔代又隔代的学弟学妹”,赢得历久不歇的掌声。 十年来我去过的省份,如吉林、辽宁、黑龙江、湖南、山东、广西,都是**次去;而访问的名城,如北京、苏州、武汉、广州,小时候也无缘一游。听众和记者常问我回乡有什么感触,我答不出来,只觉得纷沓的记忆像快速的倒带,不知道该在哪里停格,只知道有一样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像苦涩的喉核,那深刻而盘踞的情结,已根深蒂固,要动大手术才铲除得掉,岂肯轻易被记者或听众挖出。若是母亲能复活,而我又回到二十一岁,那我就会滔滔不绝,向她吐一个痛快。 我的祖籍福建永春,迄今尚未能回去,每次到厦门,都为行程所限,只能向北遥念那一片连绵的铁甲山水,也是承尧叔父的画境。中学时代整整住了七年的四川小镇,江北县悦来场,是我记忆的藏宝图中一个不灭的坐标,也是我近作长文《思蜀》的焦点。我在心底珍藏着它的景象,因为它是我初识造化的样品,见证巴山蜀水原来就如此,也见证一盏桐油灯映照的母子之情。真希望晚年还有缘回去一吊。 至于常州漕桥,我的母籍兼妻乡,也是我江南记忆的依托,今年四月五日倒是回去了一趟。那天正好是清明节,我存 和我随众多表亲与更繁的后辈,去镇外的葬场扫墓。只见好多位舅舅的葬处,墓简碑新,显系“文革”期间从他处匆匆迁来,也就因简就陋了。小运河仍然在流着,水色幸而不浊,流势也还顺畅,远远看得见下游那座斑剥的石桥,小时候那句童谣“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似乎还缭绕在桥栏杆上。此外,一切都随波逝去了,只留下河边的一大片菜花田,盛开着那样恣肆的黄艳,像是江南不朽的早春,对忙于加班的蜂群提醒:“有些东西永远是不会忘记的。” 乡愁真的能解吗?恐怕未必。故乡纵能回去,时光不可倒流。山河或许长在,但亲人和友人不能点穴或冷冻,五十年不变地等你回去,何况回头的你早已不是离乡的你了。何况即便是山河本身,也难保不变形变色?洞庭不是消瘦了么,湘夫人将安托呢?再迟去一步,三峡就不再是古迹的回廊了。 所以乡愁不全在地理,还有时间的因素,其间更绸缪着历史与文化。同乡会该是乡愁*低的层次;高层次的乡愁该是从小我的这头升华到大我的彼端。七年前我在吉林作协的欢迎会上,追述自己小时候从未去过东北,但老来听人唱“长城外面是故乡”,仍然会震撼肝肠,因为那歌声已深入肺腑;说着,竟忍不住流下泪来。未来如果有人被放逐去外星,回望地球该也会落泪,那便是宇宙的乡愁了。 韦庄词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难道老了再还乡就不会断肠吗?李清照词却可以代我回答:“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就算春色不变,而归人已老,回乡的沧桑感比起去国的悲怅,又如何呢? 孩时的旧大陆早已消逝,只堪在吾心深处去寻找。我回到生我育我的南京,但父母和同学都已不在,也没有马车辘辘,蹄声铿铿,驶在中山路旁。秣陵树当然还荫在两侧,都是刘纪文市长开路时栽植的法国梧桐,但是树犹如此,还认得当时爱坐在马车夫旁座的少年吗? 不,旧大陆我已经回不去了,迎我的是一个新大陆,一个比美国古老得多同时比美洲更新的大陆。高速公路从上海直达南京与北京,鲜明的绿底白字,说,左转是杭州,右转是无锡。以前是我在美国,用一本中国地图来疗乡愁,现在,是我在新建的沪宁高速公路上,把那张地图摊成廿一世纪明媚的江南水乡。想不到,六十年代在北美洲大平原上的逍遥游,一转眼竟能跳接到姑苏与江宁之间,通向吴越的战场,六朝的古迹。 是啊,我回去的是这样一个新大陆:一个新兴的民族要在秦砖汉瓦、金缕玉衣、长城运河的背景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纪。这民族能屈能伸,只要能伸,就能够发挥其天才,抖擞其志气,创出令世界刮目的气象来。 二〇〇二年六月于高雄 《片瓦渡海》 1 从江北国际机场出来,天已经黑下来了。毕竟是大陆性气候,正在寒露与霜降之间,夜凉侵肘,告诉远客,北回归线的余炎早抛在背后了。明蓉把我们接上工商大学的校车,平直宽坦的高速公路把我们迎去南岸。路灯高而且密,灯光织成繁华的气氛。不过长途的终点若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而抵达时又已天黑,就会有梦幻之感,感到有点恍惚不安。 说重庆是一个“陌生”城市,未免可笑。少年时代我在这一带足足住过七年,怎么形容也绝非陌生;但毕竟是六十年前的事情,沧桑之余,无论如何也绝非“熟悉”了。车向南行,渐浓的夜色中,明蓉指着对江的一簇簇摩天楼说:“那边正是重庆,你还认得出吗?”我怎么认得出呢?成簇成丛的蜃楼水市,千门万户,几乎都在五十层以上。六十年不见,重庆不但长大了,而且长高了那么多,而且灯火那么热闹,反而年轻起来。不但我不敢认他,他,只怕更不认我了吧? 第二天一早,王崇举校长就来翠林宾馆,陪我们夫妻在校园散步。校园很广,散布在斜向江岸的山坡上,高楼丛树,随坡势上下错落,回旋掩映,所以散步就是爬山。秋雨霏霏,王校长和我共伞,一面指点着寒林深涧,有山泉泠泠流来,穿石桥更往下注。他又带我们和徐学转上一条很陡的山径,青板石阶盘旋南去,没入蔽天林荫。他说这条路叫做“渝黔古道”,工商大学的校园正是起点。我们仰望一径通幽,怀古未已,王校长又带我们曲折下山,来到一个井旁。那是一口开敞的古井,宽约四尺见方,水面一片虚明。王校长说这是传说已久的仙泉,饮之可除百病,而且不论雨旱,总是水量饱满。我立刻用瓢舀了仙水,浅尝了一口,顿觉清甘入喉,又喂了我存一口。这才注意到附近的瓶瓶罐罐,散置了一地,村民或用手提,或用车推,几乎不绝于途。黄老之治的校长在一旁顾而乐之,有福与民共享。 两岸交流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访蜀,却是**次访渝。承蒙蜀人厚爱,每一次待我都像游子还乡,媒体报导都洋溢乡情。这一次回重庆,前后七天,演讲三次,前两次在工商大学与教育学院,依次是“中文不朽——面对全球化的母语”“诗与音乐”。第三讲在三峡博物馆,题为“旅行与文化”。此外,工商大学更为我安排了紧凑的日程,先后带我去了朝天门、瓷器口、悦来镇、大足石刻博物馆、江碧波画室、重庆艺术学院。 2 凡是未登朝天门北望的人,都不能自称到过重庆。因为这是水陆重庆的看台,巴蜀向世界敞开的大门。有人不免会想到三峡,不过三峡长胜于宽,历史与传说回音不断,就像河西走廊一样,与其说是大门,不如说是长廊。 门谓朝天,据说是明初戴鼎建城,依九宫八卦之数置门十七之多:朝天门在重庆半岛尖端,面向帝都金陵,百官迎接御史,就在此门。 细雨洒面,烟波浩渺,嘉陵江从西来,就在广场的脚下汇入了长江的主流,共同滚滚北去,较清的一股是嘉陵之水,主流则呈现黄褐。江面颇宽,合流处更形空阔。俯临在水域上空,重庆、江北、南岸,鼎立而三,矗起的立体建筑,遥遥相望,加上层楼背后的山影叠翠,神工之雄伟,人力之壮丽,那气象,该是西南**。 倚立在螺旋形栏杆旁边,我有“就位”之感。此刻我站的位置,正是少年时代回忆的焦点,因为两条大河在此合流,把焦点对准了。人云回乡可解乡愁,其实未必。时代变得太快,沧桑密度加深。六十年前,在这码头随母亲登上招商局的轮船,一路顺流回去“下江”的,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胜利还乡的喜悦,并不能抵偿离蜀的依依。那许多好同学啊,一出三峡,此生恐怕就无缘重见了。那时的重庆,尽管是战时的陪都,哪有今日的重庆这么高俊、挺拔?朝天门简陋的陡坡上,熙熙攘攘,大呼小叫的,多是黝黑瘦小的挑夫、在滑竿重负下喘息的轿夫、背行李提包袱的乡人,或是蹲在长凳上抽旱烟的老人。因为抗战苦啊蜀道更难,我这羞怯的乡下孩子进一趟城是天大的事,步行加上骑小川马,至少一整个下午;而坐小火轮顺嘉陵江南下,一路摇摇摆摆,马达声虐耳扑扑不停,也得耗两个钟头。那时候,泡茶馆是小市民主要的消遣;加一包花生、瓜子或蚕豆,就可以围着四方小桌或躺在竹睡椅上,逍遥半个夏日,或打瞌睡,或看旧小说与帝俄小说的译本,或看晚报,或与三两好友“摆龙门阵”。这一切比起今日的咖啡馆、火锅店,似乎太土太老旧了,但今日的重庆,新而又帅,高而又炫,却无门可通我的少年世界。 不过倚望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我仍然有“归位”的快感。人造的世界虽剧变而难留,神辟的天地仍凿凿可以指认。脚下这两条洪流,长江远从漠漠的青藏高原,嘉陵江远从巍巍的秦岭,一路澎湃,排开千山万壁的阻碍,来这半岛的尖端会师,然后北上东去,去撞开三峡的窄门,浩荡向海。这千古不爽的约会,任何人力都休想阻挡。如果黄河是民族的父河,长江该是民族的母江,永不断奶,永远不可以断奶。江河是山岳派去朝海的使者,支流与溪川,扈从无数。嘉陵江簇拥着长江,是何等壮阔的气派,这气派,到下游汉水率百川来追随,我也曾在晴川阁上豪览。 我这一生,不是依江,便是傍海,与水世界有缘。生在南京,童年多在江南的泽国,脚印无非沿着京沪铁轨,广义说来,长江下游是我的摇篮、木马。抗战时期,日本人把我从下游赶来上游,中学六年就在这脚下茫茫的江水,嘉陵投怀于母水的三角地带,涛声盈耳地度过。战后回到石头城,又归位于浩荡的下游。所以我的早年岁月,总离不开这一条母河。至于其余岁月,不是香港,就是台湾,河短而海阔,一条水平线伴我,足足三十二年。 而今重上朝天门,白首回望,虽然水非前水,但是江仍故江,而望江的我,尽管饱经风霜,但世故的深处仍未泯,当年那“川娃儿”跃跃的童心。
尺素寸心 作者简介
余光中(1928—2017) 文学家、诗人、学者、翻译家。 生于江苏南京,祖籍福建永春。曾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在华语世界影响深远,其作品被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中。 代表作品有《白玉苦瓜》《乡愁》《听听那冷雨》等。
- >
中国历史的瞬间
中国历史的瞬间
¥14.8¥38.0 - >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中国人在乌苏里边疆区:历史与人类学概述
¥26.4¥48.0 - >
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
¥15.4¥28.0 - >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伊索寓言-世界文学名著典藏-全译本
¥6.1¥19.0 - >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19.0¥49.8 - >
李白与唐代文化
李白与唐代文化
¥10.4¥29.8 - >
伯纳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伯纳黛特,你要去哪(2021新版)
¥15.9¥49.8 - >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上帝之肋:男人的真实旅程
¥19.3¥35.0